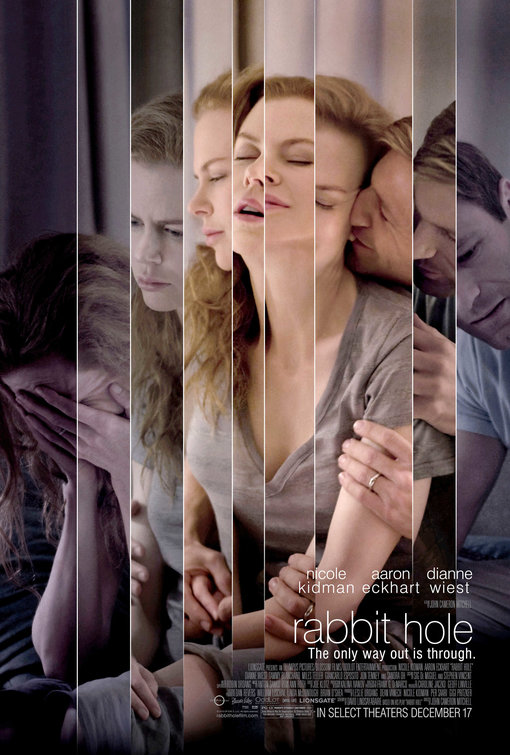一開場仿紀錄片的搖晃鏡頭, 之後一個直落長鏡頭,
跟著兄弟走過Lowell Town的長街小巷, 將沿途的鄰里都盡攝在內
最後攝影機回頭對準拍攝的工作人員, 把本片抽離投入感,
客觀地透過一個家庭的衝突, 刻劃出美國局部市鎮的文化與社會現象
開首的寫實風格, 沒有企圖把觀眾帶入故事
紀錄片的拍法, 除了說明其真人真事的改編外, 還有加強距離感的效果
看到的第一個畫面, 是直視面向兩個重心人物, 像他們在與銀幕前的人對話交流一樣
片名出現時, 鏡頭是拉遠到長鏡拍周邊環境而不是特寫兩位主角
之後在拳擊賽事時, 運用了大量電視機拍攝的角度, 時刻提醒了"在看表演"的事實
像女主持的跌倒, 台下觀眾的反應捕捉, 都是全面的看到了台上台下的互動進程
真正博鬥時亦甚少近鏡跟隨主角的動作, 如"Raging Bull" (狂牛) 的流暢攝影
多數時間是看到了全局, 在介紹出場時還不忘注入電視節目的視覺提示
如《流浪漢世界盃》中畫鬼腳的晉級過程表,
於是整套電影是在局外人角度觀賞而非主觀感受
The Fighter 在很多情節及角色上其實與 Rachel Getting Married (愛與痛的嫁期) 相類
同樣是問題家庭, 同樣是毒禍, 兄弟對照姊妹的矛盾,
甚至哥哥/ 妹妹 在嘗試擺脫毒品後回到家中, 面對 弟弟/ 姊姊 在事業/ 愛情上的突破,
情境心態上俱同出一轍, 兩者同樣粗糙具實感, 不同的正是運鏡掌握的方向
The Fighter是旁觀, Rachel Getting Married 卻是仿照家庭錄影帶手法,
希望將人帶入故事感情之中, 因而出現不少企圖營造生活感的場面, 想增強共鳴感
然而, 客觀態度的好處, 就是可看得遠大開放, 亦不用感覺到情緒像受到操控
導演David O. Russell 是以單一家庭單位喻社區, 隱含的人文關懷是低調的
輕輕帶過了警察濫用職權的段落, 以寬容輕巧的方式講濫用毒品
人種的多元性 (如柬埔寨) 更是通過鏡頭的觀察展現, 沒有刻意樣版的描繪,
對白提及Lowell只是一句起兩句止, 卻已顯出當地人對成為城市之光的重視
普遍的低學識, 低下階層的喜好習慣, 欠缺向上流動的能力, 全都在場面調度暗示了
搖滾流行曲在背景的穿插, 粗俗語言的運用, Charlene的背景學歷剖白, 都是當地文化的描述
暴力場面則展示在拳擊場的觀眾席, 酒吧內外的打鬥, 及Charlene家前的反擊
不是代表他沒有批判性, 而是他微小的細緻描寫正反映他理解問題, 亦信任觀眾的思考
而濫用毒品在當地社會的嚴重性, 則不需一言一語, 在電影中各人物的行為態度顯露無遺

他亦明白家人間的吵嚷是鬧劇, 是誇大的肥皂劇情,
背景嘈雜的聲音交集, 電話線的特寫, 都說明了其本質
把爭拗的場面配上滑稽的音樂, 把喋喋不休的家庭成員卡通化喜劇化
悲喜劇的類型通常會給予沉鬱無奈之感, 因笑話背後實是悲哀的經歷,
但本片卻有大量荒謬的笑位, 是啼笑皆非的,
不會太沉重, 同時不失喜劇感, 是客觀拍法的功力
人物的豐富立體亦是不單一主觀向主角心路歷程深鑽的成果,
每個角色不論戲份分配都寫出其獨特個性
Micky Ward 是故事靈魂, 卻是最不起眼
正因他的性格不外露, 忍氣吞聲當大哥影子多年
沒見出情緒的大起大落, 因悲哀要躲進房子中, 自處時才見其真情流露
只有後來的Charlene, 才引導出他的真感情
生活中處處忍讓, 為了合他人心意而遷就或放棄,
卻在女友鼓勵下才拾回自己的勇氣, 說出自己的心聲就讓家庭團結起來
如同擂台上他不斷的防衛, 最後卻一擊就重重讓對手倒下
他是沒有存在感的一個, 這正是Mark Wahlberg傳神之處
要低調不搶戲, 如開首兄弟同坐在畫面正中, 哥哥一直在說, 弟弟就只一直在聽
Mark Wahlberg甘於在群戲時當背景, 讓一眾成員發揮,
對角色的認真, 艱苦肌肉訓練以準備擔演的誠意, 亦可從其身形可見
Dicky與Alice則愛家人, 卻總傷害了他們, 母子間的關係也如此, 到底是愚笨還是固執?
Dicky笑稱自己是給人開玩笑的一個, 是引發笑話的悲劇人物
Alice則過度控制他人, 作為一家權威卻不自知有偏袒之心
Charlene 更是全片真正的Fighter, 在Micky家庭內打了一場又一場
與其母親的對罵互打, 與其兄長的粗口驅趕,
Amy Adams 發揮其身體語言的魅力, 像潑婦罵街卻不失女性溫柔
亦直道出片名所指, 拳賽中的Fight不比在家庭中的Fight重要, 影響這麼深遠
同時, 作為Fighter, 要為自己而打, 也要為自己所愛而打

平行剪接手法亦有助理解當下不同人物的心境取態
兄弟的對照可見於Dicky跑步節奏與Micky打拳節奏的同步,
獄中Dicky運動與練習場中Micky的訓練;
Charlene 與 Alice 爭奪兒子的段落,
從Alice 要率眾闖進Charlene家, 其對白接駁至Charlene與Micky的親熱鏡頭;
最利落的一場, 當數看紀錄片時, 不同家人的反應互接
剪接令兩小時內的起伏毫無冷場, 韻律感生活感俱備
只是結局完得突然, 像 "唔夠喉"
細想才知其戲劇重點暗中轉移, 把家庭衝突轉化為擂台奮鬥
拳賽上的勝利, 造就母親感動的擁抱
然而若失敗呢? 家中的裂痕到底是否已完全修補?
Micky是真心追求自己所想嗎?
他所指的you, you, you, 都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有可能, 或有需要擺脫嗎?
不止是母親, 其實女友同樣把自身失敗寄託在他身上,
期望若有落差, 關係會有變化嗎?
既然是真人真事, 也許就要相信這樣的理所當然了
最後, 激昂勵志的配樂, 感染力都不及一曲I Started a Joke
準確寫下Dicky的命運, 也完美的表達了母子間難以明暸的深厚感情